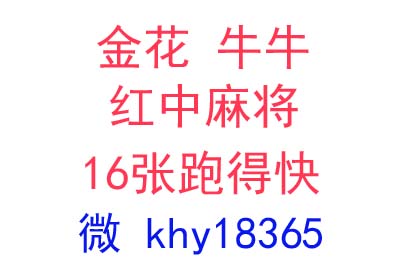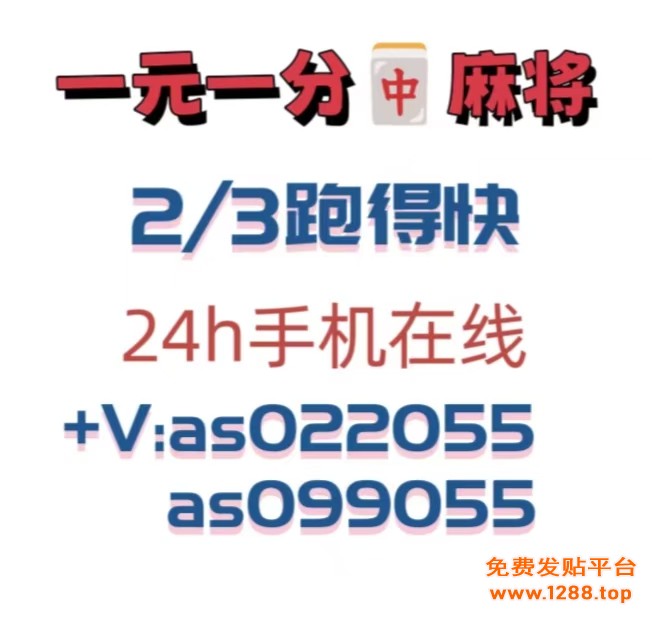发货:3天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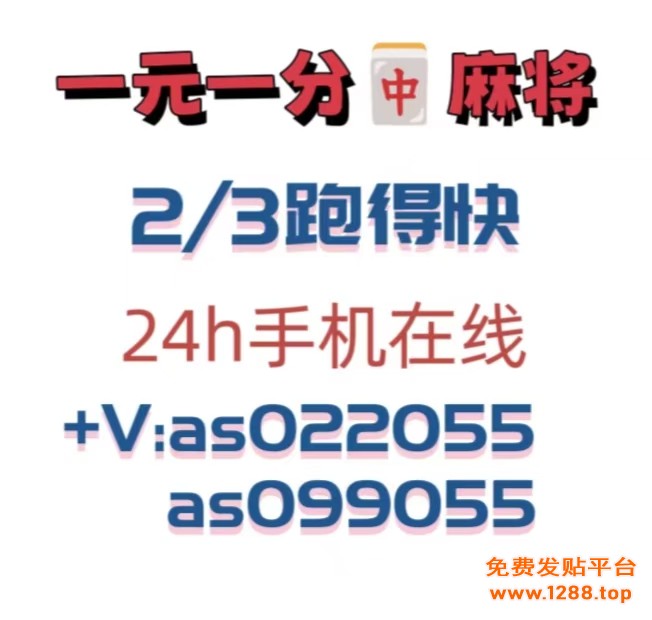
菜园里是有“菜把式”的
多少年来,我们村菜园里的“菜把式”就一个人,一直是我家对门的会儿爷爷
那时候,会儿爷爷也就五十几岁,他侍弄菜园很有一套,也真加心
菜园里经他手弄出无数条菜畦,那菜畦不能说平整如镜,可也不会有任何土坷垃
那土,细如沙状;那埂,硬得都泛起亮光
白天,他全身心地侍弄着菜园里的芹菜、萝卜、辣椒、黄瓜、茄子……;晚上,他住在不大的园屋里,与蔬菜和星星为伴
每到哪种蔬菜成熟的时候,会儿爷爷便会通知队长和生产队的会计,让他们招呼大家到菜园里分蔬菜
每家每户,担着或者是用推车推着那一筐筐新鲜的蔬菜往家走的时候,人人脸上是喜笑颜开
因为对于那时候的农村人来说,每顿饭能吃上新鲜的炒菜,可真是一种奢侈
其实,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吃饭时能吃上新鲜的蔬菜,而是常常在每天放学后夕阳西下时跑到菜园子里看牛拉水车转动,听哗啦啦的水车声
我写演义的手段很大略,即是一个记载、交谈和瓜分的进程
每部分的生长情况各别,体验也各别,然而生长中面临的题目和心路是一致的
文艺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我梳理的进程
它扶助我更好地看法我本人,同声我也经过文艺找到了一种表白自我的办法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对雨夜充满了恐惧
这种感觉来自少年时代无数个夏日的下午
记忆中,在那燠热的夏日,我总和母亲在村口的麦场里忙乎着麦子
突然,母亲说:“快摞麦”,我们就把散开晒太阳的麦捆又摞成叫作“猴顶灯”似的麦垛
在刚摞好或者快要摞好的时候,大雨往往就下起来了
多少次这样的经历,让我觉着母亲像个风水先生,能够准确地预知到一场雨的来临
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也听到了不少关于云与雨的民谚:“黑云黄边子,必能下冷子”、“石头云,砸死人”、“云朝西;泡死鸡;云朝南;水翻船;云朝东,一场空”
这样的民谚,也是我接触到的最为本质的诗歌
那时候的雨,一下就是好几天,不像现在的故乡,越来越干旱了
所以,雨夜,成为我少年时期独有的一份经历
应该说,乡村的夏夜,是属于月光、轻风、荧火虫、老槐树下唱起的童谣,它的本质是安棕的,但是,那无法终止下来的雨,夺走了我心中的美好之物,提前构成了我人生中最初的恐惧
雨哗啦啦地下着,在我心里,总觉着外面有一群密密麻麻的人在朝我走来,我也总是把这种脚步声和露天电影里看到的手提刺刀的日本鬼子联系起来--在自己的西厢房里,我独身一人,担惊受怕地捱过一个又一个无月的雨夜
谁也没有料到,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
如今我生活在城里,偶尔碰上雨夜,尽管我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灯火通明的世界,但心里也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心,总觉着在这样一个夜晚,要发生点什么
内心有些不安的我站在阳台,对面家属楼那些陌生或者熟悉的人们,要么看电视打牌,要么聊天甚至,平静地生活着
但我的心里还是有些害怕
所以,每至雨夜,我总是给朋友打打电话,或者和妻子说话
我想,这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是岁月在一个少年心里投下的阴影和这种阴影的一次显形吧
而这种显形,让我的回忆震颤不止,让我在多年之后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云的注脚被夜色收入一本没有月光的选集密密麻麻的文字里有急促的脚步声自黑暗传来
21、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我摆脱仙台之后,就有年没有照过相,又由于情景也枯燥,说起来无非使他悲观,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过程的岁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以是固然偶尔想来信,却又难以次笔,如许的从来到此刻,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像片
从他那部分看上去,是一去之后,海底捞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