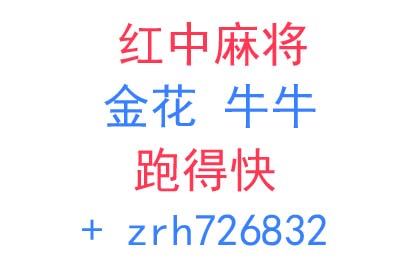列车早已驶过幼年的得意带,行驶在青涩的芳华之路上,但它对着天际长鸣一声,再次加速了速率
我似乎已瞥见芳华的尽头站牌在遥远若有若无
女孩早以泪流满面,如许的男孩怎能不让她疼爱,“抱歉,我错了,我不该把恋情当玩耍,更不该摆弄你的情绪,假如我早领会那些的话,我是一致不会如许的
”
/>小摊上卖的现炒瓜籽儿实在香,每次买了总要先推开手边的事儿嗑上半小时
这份熟悉的香,会唤起我儿时的记忆
我儿时的乡下小村,将葵花籽叫作毛嗑儿
毛嗑儿椭圆形,细长,炒熟了嗑去皮,瓜籽仁儿呈淡青色,小得不及小指甲盖儿,细嚼起来,香味满口
若是没炒,是白色的,味道清淡
记忆中的小村有一排排的土屋,屋后是一条不宽的土路,路两旁柳树葱茏,有如天然的绿色长廊
村前有一条小河,河里有泥鳅;村后是斜缓的山坡和林带,坡上有地,曾种过大片的向日葵
饱满的阳光下,我和小伙伴们在山坡上玩,身边是盛花期的葵花地,偶尔转头望过去,一大片黄艳艳的葵花让人目炫
小时候并没有觉得那片暖黄有多美,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向日葵蒲扇大的叶片
顶在头上遮阳,然后簇在小山坡上捉蚂蚁,或是用手撑着当作小雨伞而在马路上疯跑,都曾是我们最得意的游戏
田里种的向日葵,是要交“公粮”用的,以完成经济作物的任务,而院墙周围的向日葵,就是自家种来吃毛嗑儿的了
成熟的东西总不喜惹眼
当明黄的花瓣渐成深黄,枯萎,落掉,圆盘也呈黑色并向着地面时,便到了快采摘的时候了
采向日葵可是小孩子们的专利
因为太高够不着,常常几个小伙伴儿一起拉住它的杆,喊着号子,将它搬倒才行
向日葵刚斜近地面,大家便忽啦啦的争着跑到圆盘那儿,搓去盘面上的花蒂碎屑,露出怯生生的毛嗑儿
用手指抠下几粒,看看它的大小,胖瘦,便开始大喊“这个可真成(饱满)啊!”,或是有些失望的大叫“太小太瘪了!”扔一个进嘴里,嗑出的籽仁儿湿滋滋的,有着新收的清香味儿
品评过后,才拿了砍刀“当当当”的砍下向日葵“头”,收在柳条编的大笸箩里
放在阳光下曝晒,完全晾干了留待炒着吃
炒毛嗑儿可是个精细活儿
在乡下,不象现在城里用高高的铁皮回转炉,而是用做饭的大锅炒
在农闲的深秋或冬夜,吃过了饭,大人们串门拉话儿,孩子们便集在一户里炒花生毛嗑儿
灶下的火不能太旺,也不能太弱,用玉米的秸杆做烧柴最好
这时小伙伴儿们分工也很明确的,哪个添柴,哪个翻炒要有讲究
添柴的要细心,翻炒的要个大,免得烧得太猛,翻炒不及时会把毛嗑儿炒糊
先将早从村后沙地精选的白细沙倒入锅里,烧烫,再哗的一声将大簸箕里簸好的毛嗑儿倾进去,急急的用铁笊篱来回的翻
100度的白炽灯挂在大锅边的墙上,锅里腾腾窜出的烟气漫在光亮里扑着人的脸
“噼叭噼叭”声陆续响起来,拿笊篱的便急急的挥舞手臂,生怕慢一点儿会熟得不均匀
紧接着便是密集的爆响,围在周围的小伙伴们也要替翻炒的人紧张
不时的从锅里捞出来一两个放在嘴里尝,边喊着“烫死我了”边将毛嗑儿皮嗑开,尝尝籽儿仁是否已够了火候
没尝的孩子眼睛亮晶晶的望着尝的这个,急切的问:“咋样了?熟没熟?”脸上泛着馋样儿
不停的尝,还要密切注意毛嗑儿的颜色变化,翻炒的人不时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尝的人,有如正在执行一个很庄严的仪式
待一声“捞!”,他便立即将毛嗑儿从白沙中用笊篱筛出来,这时手要很麻利的,毛嗑儿通常是八分熟
若是熟到十分,再不及时散热,吃起来就会发苦,就是炒糊了
在屋外的凉夜里,大家守着炒好的毛嗑儿,边“扑扑”的吐着皮边笑闹着,欢快而又热烘烘的气氛一直温暖着今天的记忆
乡下的毛嗑儿到了城里便叫瓜籽儿了,还有被加工成五香的,各种各样
但无论怎么变换叫法儿,都是向日葵的种子,就如我,从乡村到了城里,外形言谈可能会有所改变,但骨子里仍是纯朴的农家孩子
哦,毛嗑儿,让我怀念儿时的乡村,童年的自己
时间就快到了,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等着等着,似乎听见街上敲锣打鼓的喧闹了,我急得直哭,爸爸也急得直叹气,小哥哥见安慰不了我,赶紧一溜烟跑去找妈妈了
终于,看见妈妈和哥哥急匆匆回来了,妈妈笑着抖开手中的那一团洁白:“来,快穿上试试!我在那催着裁缝师傅做完的呢!”我破涕为笑,穿着一袭白裙站到穿衣镜前,哎,真好啊!我满意地叹了口气
妈妈又给我的马尾辫扎了两朵香香的栀子花,系上红领巾,镜子里的我竟如一朵白莲了,这样想着时,不禁羞红了脸
这时,我的老师也骑着自行车匆匆来了,载着我赶忙往不远的镇上奔去
童年时候的刘姐姐年纪已经大了,再见她的时候,她那黑黑的头发已染上一层岁月的霜华,只是,那双灵巧的双手依然执著地剪着那些美丽的日月之花,她的小儿子为她申请了网页,有了她自己的艺术天地,她剪的勤快了
她剪纸轻写实,重传神,结构简洁,线条挺拔流畅,又闪耀着现代民间艺术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