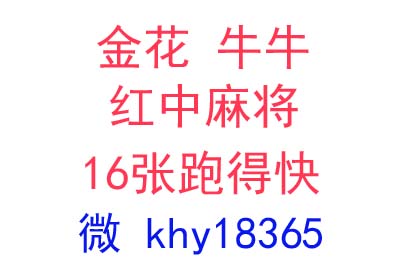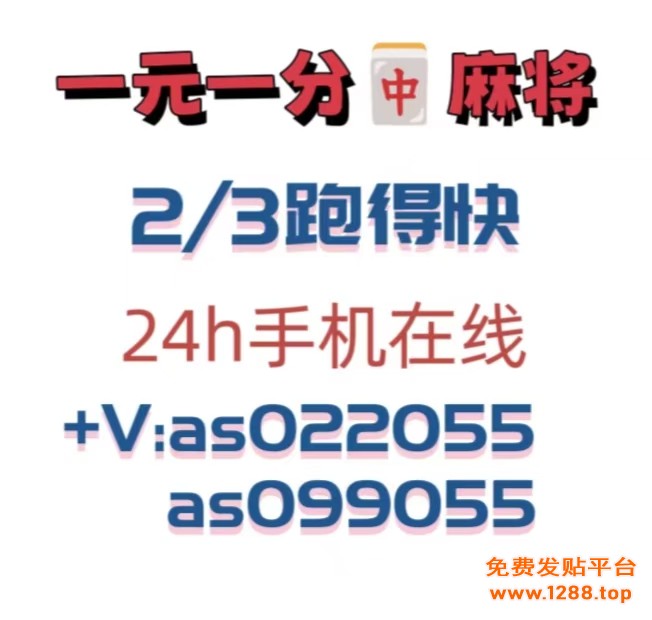
小的时候,总想爬上山顶,可是好不容易爬上山顶之后,才发现:山的后面还是山,还有更高的山顶在前面
我又爬上去,结果还是一样
我有些沮丧,一个人坐在山顶上很久很久
那一年我十三岁,我想:终有一天,我会翻过这一群山,走到山的外面去
炽热的署天到了极端,农历的六月,她们在蓄意的眼中往日了
秋发端,冷风也拂拂地州里上吹送
所以有一天,这合家的人们都到了蓄意底最飞腾,屋里底气氛实足地动乱起来
生员底心更是特殊地重要,他在庭院上连接地徜徉,手里捧着一本通书,犹如要读它记诵那么地念去――“戊辰”,“甲戌”,“壬寅之年”,总是重复地轻轻的说着
偶尔他底烦躁的见地向一间关了窗的屋子望去――在这间屋子内是有产母底悄声嗟叹的声响;偶尔他向天上望一望被云弥漫着的太阳,所以又走走向房门口,向站在房门内的黄妈问:
喜欢在大雾弥漫中独自行走,犹如踏上一条神圣的朝圣之路,尽管前方风雨凄迷,山川寥廓,人影瞳瞳,不甚分明,自有其无穷乐趣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在文人眼里自有难言的韵味和诗意,比之一览无余,更能撩人情思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即使忧伤也美的那么动人,一个“昏”字道出多少模糊的怅惘
美人深得个中秘诀,所以总是喜欢“犹抱琵琶半遮面”,让多少痴情男儿魂不守舍
雾能增添神秘感,《西游记》中神魔鬼怪的出场往往是一阵风烟过处,人影乍现,没有了风烟的伴随仿佛就少了几许魔力似的
什么东西让人一下子看穿了就没了兴味
当劳动是种快乐时,生活是美的;当劳动是一种责任时,生活就是奴役
玛克西姆高尔基
需要有真正的诗歌理想,如果说要提供一种可能的话,那么诗歌首先要求关于可能的语言和可能的美学思考
一个诗人同它作品的联系的亲疏崇卑将成为这部作品是否具有创造力(再生力)的前提
我们越来越逼近这样的命题,学者型作家是基础,是开放写作的基础,而非一种基调,切实地研究我们处境的人文内涵、史内涵对我们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