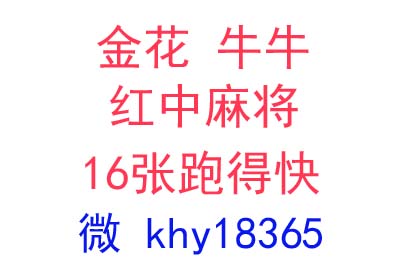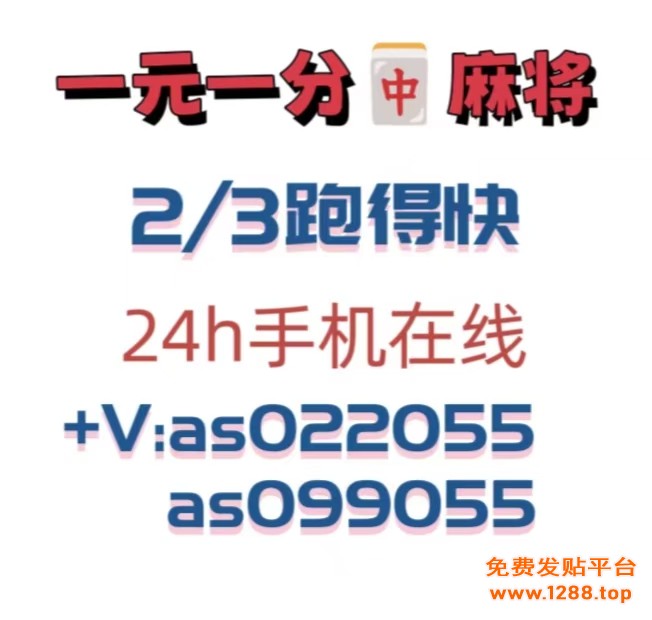
我感触本人说出口的方言不像样,奶奶想了想,说,那谁家的姑妈上回回顾,仍旧不会说方言,连半洋半土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不管是方言仍旧官语,都仍旧不会说了,依稀还能听懂少许,不过与家人交谈起来不复如未出嫁其时通顺
雨晴:一个与文学无关的写作者
琴不想回头
却又告诉我们,他曾在电话中,说不再打她了,因为儿子说如他再打妈妈,儿子就离家出走
赵树理同道吸烟抽得很凶
据王春同道的作品说,在乡村的功夫,嫌烟袋锅子抽了然而瘾,用一个山药蛋挖空了,插一根小钢管,装了一"蛋"烟,狂抽几口,才算解气
上街后,他吸烟卷,但老是抽最次的烟
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我不牢记了,只牢记是棕黄的皮儿,烟味极辛辣
他逢人引见这种牌子的烟,说是物美价廉
有一种依照大作的实质对小演义举行分门别类的,如政界小演义、城市小演义、农村小演义,我不觉得然
但即使从谈话的观点看,这种分门别类倒是适合地指出了某些作者谈话上的程式化
此刻的情景常常是:政界小演义大多是嘲笑的、嘲笑的、观念化兼具典范化的,颇有些放荡不羁,字字句句渗透来的都是政界“底细”和政界“形而上学”
城市小演义则多是虚无轻盈的情结,谈话显得随便、懒惰、发飘
农村小演义犹如好些,或简略,或抒怀,但平淡无奇过多、颜色不够充分……我蓄意的是,不妨从那些写尽政界起落沉浮、城市实情假冒、农村酸甜苦辣的大作中感遭到,各别的作者,由于体验、体验和常识档次的分辨,而展现出充分多彩、绰约多姿的天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