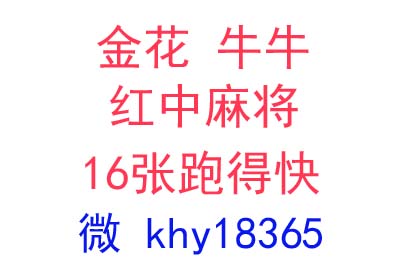诚信可免押进亲友圈验亲友圈,满意再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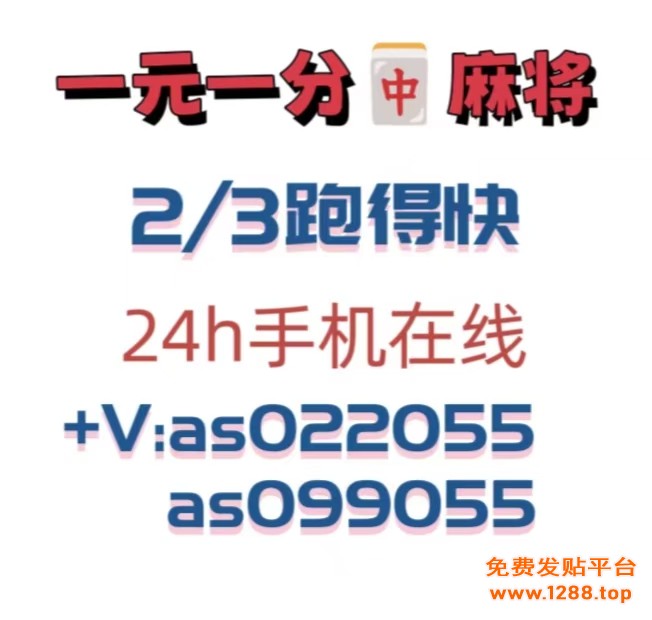
2004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余光中集》,受到广泛注意;2004年4月,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开奖,余光中成为2003年度散文家奖得主
近日报刊上关于他更是连篇累牍,“文化乡愁”、“中国想象”、“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之类的溢美之辞让人头晕目眩
今年4月21日的《新京报》上,一位记者在其“采访手记”中这样写道,“高尔基提前辈托尔斯泰‘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儿’,况且曾相见并有过一夜谈呢?”他将余光中比作托尔斯泰,并为自己能见到这位大师而感到幸运万分,这段“惊艳”之笔将大陆的“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
遗憾的是,这些宣传和吹捧说来说去不过是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和美文,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毫无认识,因而对于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并不清楚
不过,对于普通的读者也许不应该苛求,因为大陆对于台港文学一向隔膜,而余光中又善于顺应潮流
举例来说,在九大卷300余万言的《余光中集》中,余光中的确是十分干净和荣耀的,因为他将那些成为他的历史污点的文章全部砍去了,这其中包括那篇最为著名的被称为“血滴子”的杀人利器《狼来了》
但在行家眼里,这种隐瞒显然是徒劳的,每一个了解台湾文学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此事,海峡两岸任何一本台湾文学史都会记载这一桩“公案”
乡土文学之争 余光中在台湾文坛上的“恶名”,开始于“唐文标事件”
70年代初,台湾文坛开始对一统台湾文坛的“横的移植”的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批评反省,其标志是唐文标先生的系列批评文章,他在1972年到1973年间的《中外文学》、《龙族文学评论专号》、《文季》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诗的没落》等文章,批评台湾现代诗的“西化”和脱离现实的倾向
这一系列文章在文坛引起了震动,引发了关于现代诗以及现代主义的大争论
在这场论争中,余光中当时是维护现代诗的代表人物
关于论争的是非本身,这里无需加以评判
想提到的是,余光中一出手就显示出他的不厚道
在《诗人何罪》一文中,余光中不但言过其实地将论争对方视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而且给对方戴上了在当时“大陆”的台湾最犯政治忌讳的“左倾文艺观“的帽子
所以就有论者揭露余光中搞政治陷害,如李佩玲在《余光中到底说了些什么》一文中指出:“这样戴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标(也算得上是压迫知识分子了吧),还在吓阻其他的人
” 但这样的批评对于余光中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70年代后期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变本加厉地施展了他的攻击手段,并且与国民党官方、军方配合申伐左翼乡土作家
在这场乡土文学论战中,台湾乡土文学受到的最大攻击来自两个人,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另一个就是余光中
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
1977年7月15日至8月6日,彭歌发表了系列官方文章,强调“爱国是基本的大前提”,不是“蹈入了‘阶级斗争’的歧途”
紧随其后,余光中在8月20日《联合报》发表了《狼来了》一文,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工农兵文艺”
他在此文开头大量引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以此证明台湾乡土文学的思想与前者的相类,并且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
”接着,他从攻击大陆的共产党文艺统治谈起,抱怨台湾的“党治”未免过于松懈,对于乡土作家过于客气: “
“是啊,彼得,你上我这边来是对的,”生疏人说,“此刻,我来报告你,你瞥见的不是菜田主人的浑家,而是你本人的浑家;他瞥见的也不是菜田主人,而是你
是你恫吓了她,她恫吓了你
尔等做贼胆怯,就认不清人啦
跟我走吧,你将变成我最要害的伙伴,我的得力帮忙
我是耶稣
”
其实,一切都是简单的,当它生成了种子的那日,被风剥去表皮,又慢慢被尘埃和泥土掩埋在视觉之外,许多目光就再难以发现它们的存在
而后,它们就会在某个时刻突然地冒出人类的地面,并逐渐往高处生长
一棵树和另一棵树,我可以从它们彼此并不相互关联的中间找到这样一种关系:无关的、有关的、矛盾的、还可能有着伤害的那种,如果它们挨得太近,彼此影响了生长,它们同时都不能向对方延伸
一个就会成为另一个地狱,它们互为牵制,并阻碍
45、曾经爱旳轰轰烈烈,,如今旳如今却是爱旳浅浅淡淡
老姥娘家住在很远的一个小山村里,从姥娘家走,要顺着那条河坝路一直往西,过一个村庄,再过一个村庄,又过一个村庄,直到我都累得想哭了,直到觉得已走到大山的尽头了,才在山坳里看到那个小小的村子
姥娘说,我们走了十五里路